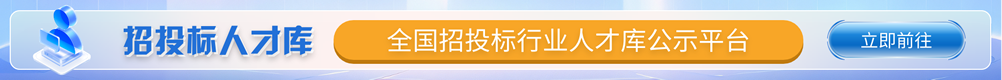白日·洛桑扎西、張丹 ▎桑耶寺桑丹林大日如來石刻圓雕造像的發現及意義
所屬地區:西藏 - 昌都 發布日期:2025-07-31發布地址: 青海
白日·洛桑扎西,藏族,教授、博士生導師,西藏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2018-2022年教育部高等學校美術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西藏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西藏大學“珠峰學者人才發展計劃”高原學者、西藏自治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專家委員會委員、西藏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西藏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西藏博物館特聘研究員、西藏收藏家協會理事、拉薩市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審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城市雕塑家協會會員;自1994年以來在各類刊物上發表三十多篇學術論文,其中在CSSCI來源期刊上發表的主要學術論文有:《論藏傳佛教微型雕塑嚓嚓在藏區的傳入與工藝研究》《藏族模制微型雕塑嚓嚓及其工藝特征》《艾旺寺造像藝術風格再探》《尼塘寺早期彩塑造像風格討論》《扎塘寺壁畫風格研究》《再論早期藏式佛像美術風格》等;多次參加過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并做交流和發表學術成果;主要雕塑作品:《古韻》被長春世界雕塑藝術公園雕塑藝術館永久收藏、《母子》被西藏美術館永久收藏。曾編著:《繪畫與裝飾》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丹巴熱單作品集》(副主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藏族美術大集成·雕塑藝術·石雕·西藏卷1》四川民出版社出版2018年、《指尖古韻-扎囊民族手工藝》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藏族美術大集成·雕塑藝術·石雕·西藏卷2》四川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12月。主持國家教育部重大項目《西藏宗教藝術-宗教雕塑》、國家社科基金西部藝術規劃項目《早期藏式佛教美術風格研究》、承擔挪威合作網與藏大合作項目《藏族壁畫藝術》和《金銅鑄造工藝》、國家圖書出版基金項目《藏族美術大集成》之《雕塑卷1-14卷》、主持藏大與尼泊爾特里普文大學合作項目“金屬失蠟法鑄造技術開發推廣項目”、 參與中央電大教材《藏族美術鑒賞》的編寫、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者個人項目:《西藏彩塑藝術遺存調研與保護對策研究》、主持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文藝扶持項目《幸福生活系列雕塑作品》等項目。
張丹,西藏大學藝術學院2020級博士研究生。?
摘要:2021年,在桑耶寺修繕過程中,從轉經道路基下挖出一塊石刻造像圓雕殘件,這塊造像的體量足有真人大小,僅存造像軀干,與一直存放于桑耶寺桑丹林佛殿院內的一塊石刻圓雕殘件適配,這塊石刻殘件恰好僅剩下造像半身,而且在造像的座臺前面留有兩排略有缺失的藏文石刻題記,為研究和了解石雕造像的歷史背景提供了線索。佛教文化對藏族石刻藝術的推動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創作了石板石刻浮雕、摩崖石刻群和斯烏蔡黑石雕刻以及石胎泥像等種類繁多、精美絕倫的石雕造像作品,但是這種相對大尺寸的純石刻圓雕造像遺存在衛藏地區乃至整個青藏高原實屬少見,因此這塊石刻圓雕殘件的出現對研究藏族傳統雕塑藝術發展史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研究價值。文章根據實地調研并結合既有研究和文獻資料,初步討論了這件石雕殘件的表現題材、原作歸屬、雕刻手法、雕刻時間和造型風格以及發現的意義。
關鍵詞:桑耶寺;大日如來;石刻圓雕造像;藏傳佛教
隨著佛教傳入青藏高原,藏族與周邊地區各民族之間建立了以佛教文化為紐帶的廣泛交流。8世紀,藏傳佛教第一座佛法僧俱全的寺院-桑耶寺建造完成,意味著佛教文化在青藏高原扎根立足。不可否認,佛教激發了藏族傳統文化的活力,佛教的造像藝術作為重要的弘法、助修載體,也豐富了本土視覺藝術的表現形式。僅就表現佛教造像的雕塑工藝來說,可謂百花齊放。在這個時期的桑耶寺范圍內為造佛塑像就采用了多種材料的雕塑表現手法和技藝。有明確文獻記載[1]的雕塑材料種類多達近十種,其中包括彩塑、木雕、金屬鑄造、金屬鍛造、熱斯(??????? 近似干漆夾苧工藝)、皮塑(??????? 郭斯)、石雕和石胎泥像等技藝,開啟了富有區域文化特色的藏傳佛教造像藝術傳統。這個時期正值藏傳佛教前弘期,在外來佛教美術的影響下藏族雕塑藝術,尤其石刻藝術發展迅猛,中原內地以及尼泊爾和克什米爾等地佛教藝術家們共同參與制作的佛教作品眾多且不乏高質量珍品,其中就有桑耶附近的松卡石塔群、烏孜大殿的主尊能仁大圓覺釋迦牟尼石胎泥像以及芒康囊巴朗贊拉康石雕群[2]、昌都察雅仁達摩崖石刻(804)[3]、香堆鎮向康石雕群[4]、毗朵摩崖石刻群(806)[5]和査果西溝石刻以及嘎托鎮大日如來摩崖石刻群等[6],這些遺跡石刻表現手法多樣,既有圓雕,又有浮雕。浮雕主要用于石板石刻和摩崖石刻的造像表現中,類型有高浮雕、淺浮雕、陰刻線浮雕等;圓雕手法有兩種類型,即完整或純粹的石刻圓雕和石雕與泥塑手法相結合的石胎泥像手法。赤德松贊在位時期(798-815)是藏族歷史上摩崖石刻興盛的時期,不僅留下很多較大規模和體量的石刻群,同時也有瓊結藏王墓守墓石獅和瓊結石碑、嘎瓊拉康石碑以及杰拉康石碑等多個具有較大影響的石碑。
本文將要討論的石刻圓雕作品就屬于前弘期以桑耶寺為中心的雕塑藝術蓬勃發展的這一關鍵時期的石刻造像遺存,具有特殊的文化藝術價值和意義。
圖1?網傳桑耶寺桑丹林石刻圖像
圖2?安放于桑丹林院的石刻座臺線描圖(范怡嵌繪)
2021年,桑耶寺圍墻內轉經道的修繕過程中,桑丹林(也稱虛空靜慮洲)佛殿附近的路基下,施工人員挖出了一塊有人為加工痕跡的石刻殘件(以下簡稱殘件1),發現其為一尊報應身裝束的造像上半身像,之后,新發現的造像殘件圖像開始在網絡上傳播(圖1)。為進一步了解石刻殘件的信息,筆者先后多次前往桑耶寺現場調研,在寺院僧人洛桑旦增等的熱心協助下,采集了石刻殘件的相關信息。我們發現石刻造像頭戴碩大的三葉寶冠(冠葉長度為臉長的1倍),冠葉圖飾為卷草紋樣,正面為偏方形的長冠葉,冠葉頂部受損,左右兩邊為三角形的小冠葉,雙耳佩戴連珠裝點的大圓耳環,除了下顎部位略有破損之外,面部保存相對完好,天庭飽滿,慈眉細眼,平滑的臉頰上還能依稀看到泥金的殘存,雙唇依稀殘留著朱砂色,可見是直接彩繪的石刻圓雕,頸部三紋下配有雙排連珠項圈,造像雙臂缺失,佛衣簡潔貼身,僅見褶紋疊壓層次清晰的絡腋[7]斜挎胸前(圖1),整石豎立后的總高度在100cm左右。這塊體量較大的石刻殘件被發現之后,我們自然聯想到了保存于桑丹林殿院內的另一塊僅存方臺與造像下半身的石刻殘件(以下簡稱殘件2)。這件石刻殘件安放在這里至少已有近四十年(目前已經搬離),經過現場詳細比對之后,我們發現由于兩件石刻受損嚴重,軀干部分和下半身的上下銜接處缺少完整的接口(圖2),但是兩塊殘件的石材、雕刻工藝和造型比例均符合同一尊造像的可能性。尤其兩塊殘件背后保留有一條10cm見方的方體豎條石,軀干上的方條石始于枕骨部位,完全可以與石刻殘件下半身部分的方條石上下拼對,即有可能是原造像配有背屏,應該與背屏形成榫卯接口,方體石條可能是銜接的榫頭(圖3),因此我們確信這尊缺失雙臂而僅存造像軀干的殘件1就是桑丹林的遺存,且與長期安放于此處的下半身石像殘件2是一個整體。從殘件2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造像的雙手施以禪定印,雙腿結金剛跏趺坐姿,雙膝頭均遭到破壞,造像的座臺只配有方形坐墊,未見常規的蓮花座,總高度為44cm。其中方墊厚10cm,兩件石雕殘件復合還原后坐像通高為130cm左右(圖4),基本為真人大小的尺寸,表現內容應該為五方佛之報應身裝束的大日如來,也稱毗盧雜那佛或朗巴朗增佛,是繼發現昌都芒康縣邦達鄉境內囊巴朗贊(大日如來)拉康內的五種性佛石刻造像群[8]和昌都市察雅縣香堆鎮向康大殿石刻群[9]之后的相關石刻圓雕遺存的又一大重要發現。同時,我們發現,原保存于桑丹林院內的殘件坐臺正面刻有兩排清晰的藏文題刻,雖然受損殘缺而不完整,但也有一定的信息量,是破解石刻造像歷史背景的重要線索,值得深入探討。
圖3?桑丹林石刻側面圖(范怡嵌繪)
圖4?兩件殘件的電腦合成示意圖
桑耶寺桑丹林屬于早期殿堂史料記載,來自中原內地大乘和尚“摩訶衍”(??????????????)就曾在桑丹林傳播禪宗,因此桑丹林應該是閉關修行的專門場所,獲得了王室家族成員的追隨,即藏史中所記“頓門派”的活動場所。記述桑丹林佛殿造像信息的代表性歷史文獻主要有以下幾種:
1.《韋協》記載:“在桑丹林供奉有父王的極具加持力的毗盧雜那佛為主的五種性佛以及從尊十六聲聞佛弟子。”[10]
2.《巴協》記載:“在虛空靜慮洲中,以父王的極具加持力的本尊毗盧雜那佛為主的五種性佛和聲聞十六尊。”[11]
3.《娘氏宗教源流》記載:“在虛空靜慮洲中的造像群有極具加持力的本尊毗盧雜那佛為主的五種性佛和盛世成就十六菩薩,即二十六尊。”[12]
4.《司徒古跡志》一書記錄了桑丹林殿中的佛像:“位居西面的桑丹林佛殿中,真人大小的石雕毗盧雜那佛配有金銅花冠,四方佛,四尊母性菩薩和四尊父性菩薩,兩尊金剛等均為藥泥塑像。外邊院落墻面上鑲嵌了一肘高的精雕石刻浮雕千佛,千佛石板石刻浮雕由攝政王德墨仁波切阿旺江白德列加措所主持建造。”[13]可知桑丹林主尊為真人大小的石刻大日如來佛像,八隨佛弟子為藥泥材料的彩塑像,此時,石刻的原有冠葉上后期套上了金銅花冠。
5.《桑耶寺簡志》記載:“桑丹林,該林位于西大門強巴林北側,‘文革’時毀為廢墟。建筑坐東朝西,據說原來主供五尊一米多高的石雕像(一佛四觀音),解放前,三尊搬藏于乃東昌珠寺,二尊破碎石像至今還在桑丹林廢墟上。”[14]在這里所指二尊破碎石像是否為眼下我們所看到的兩塊石像殘件還是獨立的兩尊石像,也需要進一步證實。因為昌珠寺中的石雕遺存屬于石胎泥像,而目前所見殘件1和殘件2屬于純圓雕石刻作品,是兩種不同的石刻工藝。
6.列謝托美編寫的《桑耶寺志》記載:“在虛空靜慮洲中,供奉有以父王赤德祖丹的極具加持力的本尊依執(佛像)、迎請自澤當貢布山的毗盧雜那佛為主的五種性佛和環繞著主尊的盛世十六尊菩薩。繪畫有擺脫惡道的情景,回廊中繪制有眾佛陀的形象,此佛殿為閉關之所(目前閉關所已重建),護持神為銀首王。”[15]
綜觀以上文獻信息,首先,從《韋協》《巴協》《娘氏宗教源流》的記載斷定,桑丹林佛殿中供奉的主尊是“父王極具加持力的本尊毗盧雜那佛”,即大日如來佛;其次,從《司徒古跡志》《桑耶寺簡志》《桑耶寺志》中可以看出有兩尊石像或者有一尊石雕的毗盧雜那佛,至少可以確定有一尊石刻造像,尤其在《司徒古跡志》中明確記載桑丹林主尊佛像毗盧雜那佛是一尊真人大小的石雕造像,而其余為藥泥彩塑像,這一信息與近期發現的石刻造像內容與尺寸大小完全一致。另外,成書于20世紀初的《司徒古跡志》中記載的菩薩數量與其他史書記載不相符,其他早期的資料都顯示桑丹林殿內塑造有16尊菩薩像(8尊母性菩薩和8尊父性菩薩),而且這一數字應該是最初的準確數據;而《司徒古跡志》中記載僅有8尊菩薩,這一記錄有兩種可能:一是司徒的記錄出現了遺漏,二是后期遭受破壞后很有可能選擇性地補塑了八大菩薩像,而且是4尊母性菩薩和4尊父性菩薩。必須注意的是,《司徒古跡志》是依據當時實地調研的數據,其他史書中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巴協》《韋協》等文獻資料。另外,如《巴協》《韋協》等早期史料未曾提及大日如來的造像材質,而《司徒古跡志》通過現場考察記錄明確記載供奉有石刻造像的信息,且記載十分詳細。因此,這尊石雕毗盧雜那佛主尊像很有可能是后期替換主尊造像的材料或遭到人為破壞后重塑的。這種事件在歷史上也曾有出現,譬如昌珠寺著名的五種性佛中三尊佛像確定是石雕像,而另外兩尊為泥塑像,到了18世紀時,五世達賴喇嘛補塑了兩尊合金造像替換兩尊泥塑像。[16]因此,如果桑丹林中供奉的這尊毗盧雜那佛造像也為后期補塑的或者材料替換的話,那么何時替換、為什么要替換補塑等問題都非常值得探討。
如前文所述,與新發現石雕殘件1相符、保存于桑丹林殿院中的石刻殘件2上,有一排非常重要的題刻文,是揭開這尊造像相關信息的關鍵線索。我們發現座臺正面的兩排題刻雖然有些殘缺,但是在題刻上赫然出現了3位歷史人物的名號,雖缺字少文,但是人物名稱結構清晰、人物關系較為明確,因此基本克服了殘缺的不足,具體題刻內容如下:
第一排:??????????????????????????????????????????????[17]
第二排:????????????????????????????????????????????? ?????????????????????
大意為:第一排:×松德贊在位時期石上大日如×
第二排:為歸天后的×德松贊積功德,妃子赤莫列×[18]。
顯然,這是在敘述石刻造像的雕刻時間和用途以及供養人的信息,很遺憾銘刻文的前部和后部均殘缺不全,但是借助史料對所涉及的3個人物名稱進行推論,似乎是桑耶寺建造時期的父王赤松德贊和其子赤德松贊以及赤德松贊的妃子覺姆赤莫列。從佛像方形座臺前面的銘刻文上可以推論造像的雕刻年代應該是9世紀初,至少銘刻文是赤德松贊去世后雕刻的。而且,赤德松贊的妃子(覺姆)赤莫列的名號處于供養人的位置,因此題刻上出現的3位歷史人物的名稱中完整的“覺姆(妃子)赤莫列”的名稱書寫準確無誤。這一關鍵人物的出現能夠確定造像雕刻的基本年代或上限年代,也可證實坐像為大日如來佛像。
綜合文獻記載可知,石雕銘刻文中的覺姆(王妃)赤莫列(??????????????????)就是赤德松贊的三妃子之一的卓撒赤莫列(?????????????????????),而這個稱呼是《賢者喜宴》作者引自贊普赤德松贊的誥文,因而有一定可靠性。赤德松贊繼位娶妃時已在806年之后。因此此尊石雕造像很有可能是后期住在康區的更·仙蒂的舉薦之下,覺姆(王妃)卓撒赤莫列主持募捐,并對桑耶寺進行維修時補塑的。[19]再者,被視為桑耶寺簡志的《巴協》《韋協》等文獻中特意記載了桑耶寺范圍內除了泥塑之外的特殊材料的造像,比如烏孜大殿的主尊能仁大圓覺(???????????????)釋迦牟尼是石胎泥像作品,烏孜大殿二樓的漢式造像群和江白林殿的佛像塑造采用了皮質雕塑工藝,三樓的印式佛像的塑造采用了干漆夾苧類型的綜合材料雕塑,等等。因此,按慣例理應記錄桑丹林主尊造像的材料,但是我們沒有發現有關特殊材料的記載,由此也可以推測此石雕像是后期補塑的可能性。按正常的推論,桑耶寺作為赤松德贊所建的歷史事實,《巴協》中“以父王的極具加持力的本尊毗盧雜那佛為主的五種性佛和聲聞十六尊”一句中的“父王”理應指赤德祖丹,而在石刻銘文中殘存出現的3位人名及相互關系來推斷,上行所見的“□□??????????????”應該是指赤德松贊的父王赤松德贊,而“??????????”應該是指赤德松贊,與緊接著出現的“??????????????????”(覺姆·赤莫列)的人物關系相呼應。
從造像年代來說,《贊普赤德松贊小傳》[20]認為依據藏族歷史上唯一一次的年號“彝泰”(?????????)的紀年時間來斷定贊普赤德松贊(798-815在位)[21]的去世時間可以確定為815年,與漢史記載816年的時間基本相符。那么,石雕銘刻題記中顯示的“為×德松贊仙逝所造”的大意來分析,雕刻此尊石雕的時間可以斷定為815年之后,也就是其父赤松德贊(755-797在位)去世的第18年之后;桑耶寺(建造時間:775-787)建成的第28年之后。根據《巴協》中的記載:“一段時間,桑耶寺已無僧人供養,無秩序可言,寺院內部滿地為老鼠屎,佛殿的門板也已不翼而飛。此景被住在康區的更·仙蒂聽說后,極為不悅,帶著請示回到衛藏,向卓撒赤莫列匯報。”[22]在這里,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早期文獻對桑丹林佛殿內主尊佛像大日如來都有一個相同稱呼,即“父王的極具加持力的本尊毗盧雜那佛為主的五種性佛”(??????????????????????????????????????????????????????????)。這里所提及的“父王(???????????)”應該是誰?桑耶寺的建造者赤松德贊之父赤德祖丹還是赤德松贊之父赤松德贊?桑丹林作為桑耶寺最初的佛殿之一,供奉其中的主尊佛像被稱作“父王的極具加持力的本尊毗盧雜那佛”,那么,按常規的提法在此所指“父王”理應是赤松德贊之父贊普赤德祖丹;但是王室內真正修行大日如來始于赤松德贊時期,[23]在此所指“父王”為贊普赤松德贊的可能性非常大,該殿堂內的佛像應該是其子赤德松贊時期或赤德松贊之妃子覺姆(王妃)赤莫列主持修繕,也就是說,桑丹林佛殿很可能屬于建寺不久后遭到破壞而被王妃覺姆赤莫列等人募捐修復的殿堂之一。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赤松德贊之父赤德祖丹沒有真正意義的實修記載,所以與“具有特殊加持力的本尊佛像”的提法不相符;第二,赤德松贊時期對父輩所修寺院進行了全面的維修;第三,赤德松贊之妃覺姆赤莫列曾募捐財物,修繕過桑耶寺的部分殿堂。桑丹林作為早期佛堂建筑遺存,對所供佛像稱“父王的本尊佛像”,應該是赤松德贊的后人為其所供,如果屬于當時的佛像就應該是“贊普”的本尊佛像來稱呼才合乎常理。因此,從多種角度來看,這批佛像群在后期修建的可能性極大:首先,題刻中對赤松德贊“父王”的稱呼;其次,赤德松贊已歸天的表述和覺姆(妃子)赤莫列名號的排序上也合乎常理,也透露出了這尊石像鑿刻于815年之后的時間信息,因為如前所述赤德松贊去世于815年。[24]綜合匯總文獻記載,為我們提供了以下幾點重要信息:
1.桑丹林的主供佛像確實是一尊大日如來佛;
2.從多個版本的早期文獻中“父王的本尊依執(所依)大日如來”的表述語氣來分析,造像出現的時間應該晚于赤松德贊在位時期;
3.從造像數量的變化來說桑丹林在歷史進程中多次被破壞;
4.從離現在最近的一次實地考察記錄[25]來看,桑丹林主供主尊佛像確實是真人大小尺寸的一尊大日如來石刻造像,后來成為兩塊殘件,與當前我們所掌握的殘件數據相符。
綜上所述,赤德松贊去世后,其覺姆(妃子)赤莫列主持在桑丹林供奉了一尊真人大小的石刻圓雕大日如來造像和藥泥塑造了隨佛弟子群像。一方面修繕了父輩的本尊佛像,同時也為積功德、超度亡靈。
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顯示,桑耶寺范圍內雕刻于吐蕃時期的石刻圓雕作品僅有兩處,一處是以早期《巴協》為代表的史書中記載的烏孜大殿主尊能仁大覺石胎泥像;另一處是后期以《司徒古跡志》為代表的20世紀之后的文獻中記錄的桑耶寺桑丹林毗盧雜那石刻造像。其中,前者是石胎泥像,后者是石刻圓雕作品,兩件石雕均屬于石刻圓雕手法的作品,但是屬于兩種不同的工藝表現手法。
關于烏孜大殿主尊能仁大覺石胎泥像,最初從“亥布日”山上迎請時,文獻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此時贊普正苦思冥想,造何種佛像供奉于殿內,忽夢見一白衣人言道:‘尊王您要塑造的佛陀和眾菩薩像昔日曾被世尊加持過,我將一一示于你’,于是又夢見登亥布日山時,看遍眾多巖石塊,只見白衣人手指某一石塊說此乃是某某如來佛,又指另一石塊誦念那是某某菩薩,被呼作忿怒明王的石像也被一一指出。次日拂曉,贊普起身即刻上山尋覓,只見巖石上的佛像大致如夢中所見一般。贊普大喜,宣召泥婆羅石匠,下令按所見石像塑造佛像。”[26]也就是說當時是由尼泊爾石匠負責完善這尊石胎造像的,最終以泥塑來細化和增加體量的方式完成了這尊藏式風格的烏孜大殿主尊釋迦牟尼石胎泥像。與之相比,近年在桑丹林殿周圍發現的石刻殘件顯示了完整的石刻圓雕手法,尤其從造像頭發處殘留的石青顏色和佛面部殘留的金汁以及唇部殘留的朱砂色都能證明,當然從細化的造像配飾和五官的刻畫上也能直觀感受到這是一尊精美完整的石刻圓雕作品。造像配有三葉寶冠,中間冠葉雖有殘損,但是可以看出略呈偏長方形,左右兩邊的冠葉呈三角形,僅從這一點可以顯露出流行于8-10世紀鮮明的尼泊爾造像風格冠葉特征,冠葉中央豎排的3顆珠寶和邊緣卷草紋的裝飾顯示出8-10世紀左右印度波羅風格造像影響下的尼泊爾造像特征,人物面目略顯內斂、平和的神態以及胸前斜挎的簡潔單薄的絡腋或梵繩褶紋,均顯示出吐蕃時期的主流佛教造像風格,即一種以尼泊爾造像風格為主兼具地方特色的雕塑風格,尤其上下唇更像是特定時代的標志,這一點從與美國魯賓博物館收藏的一尊吐蕃時期金銅造像作對比便一目了然(圖5、圖6)。如果我們拋開雕塑材料的隔閡,用線描圖來比較就能看到兩件作品在造型風格和神態氣質上具有極其相似的時代氣息。同時在加德滿都帕坦一帶李查維晚期[27]的石刻造像遺存中可以得到旁證。我們并不清楚桑丹林殿的石刻造像是否也有可能是尼泊爾石匠所為,但其深受尼泊爾造像風格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尊大日如來石刻圓雕造像未配蓮花座,應驗了貢欽·晉美林巴談到祖拉康(在此應指桑耶寺)的大佛像有時不配蓮花座的說法,同時也顯示其時代造像特征。[28]
圖5?吐蕃時期/收藏于美國紐約魯賓藝術博物館
(范怡嵌繪)
圖6?桑耶寺桑丹林石雕殘件線描圖(范怡嵌繪)
桑耶寺建寺之初的造像材料豐富、工藝種類繁多,有文獻明確記載的就有石胎泥像、彩塑、石雕、皮塑、熱斯和金屬造像等。同時造像風格也有早期藏式佛像風格、漢式風格、印式風格、尼泊爾風格和斯瓦特風格,等等。
桑耶寺發現的這塊吐蕃時期石刻圓雕造像殘件,一方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藝種類的補充,填補了此處純石刻圓雕造像的工藝種類,對西藏雕塑藝術的發展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在同時期同一點上出現這種石刻圓雕造像技藝的作品,反過來證明當時出現的石胎泥像技藝并非為石雕技藝的不成熟而借助泥塑的二次塑造,而是獨立、成熟的一種塑像技藝。
同時,桑丹林大日如來石刻造像的出現說明,8世紀在桑耶寺的建造過程中不僅采納了石胎泥像的古老工藝,同時也有石刻純圓雕造像的工藝,雖然兩者同屬石刻圓雕的門類,但是工藝上有著本質的區別。石胎泥像的石雕造型雖為圓雕,但它僅僅是彩塑造像的內胎,無材料的美感可言,更沒有具體的審美追求,一定程度上省去了細節刻畫的環節;與之相反,純粹的石刻圓雕是另一種表現形式,可以從四周觀賞的同時,一步到位地刻畫造像的所有表層細節,使其具備一種石雕的雕飾和材料美感。桑丹林石雕作品的雕刻師身份為何不得而知,但是從石雕殘件上展現出來嫻熟的雕刻技藝和對石材的駕馭能力上可以斷定該作品絕非偶得,如此精美的石刻作品出現在藏傳佛教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點和重要時刻,使其具有了除宗教意義之外的社會的、文化的交往交流等方面的意義。
在西藏石刻藝術的發展歷程中,除了小型的寶石類或印度“斯烏蔡”黑石雕刻[29]及其影響下的小尺寸石刻圓雕作品外,有關藏傳佛教前弘期石刻圓雕的遺存、遺跡和文獻記載極其稀少,目前所發現的尺寸超過50厘米以上的除了桑耶寺桑丹林的石刻殘件之外,僅有昌都芒康縣邦達鄉境內的囊巴朗贊(大日如來)拉康內的大日如來佛像和八隨佛弟子的石刻造像群、昌都市察雅縣香堆鎮向康大殿內主尊囊巴朗贊與八隨佛弟子等內容的部分殘件等3處代表性的石刻圓雕造像遺存。其中昌都邦達囊巴朗贊石刻造像風格屬于早期藏式佛像風格[30]類型,而香堆鎮向康的造像里能夠看到一絲中原內地造像的影響,尤其從蓮花座臺、面部輪廓造型以及眼部為主的五官的刻畫上均有體現,而桑耶寺新近發現的石刻造像殘件上較為清晰地看到前弘期在衛藏腹地較為盛行的尼泊爾造像風格的影響。
香堆鎮向康內菩薩殘件的發髻高聳,三葉冠,冠葉形制大小相近,冠葉呈弧尖三角形,面相平和,上眼瞼較平直,下眼瞼下弧較明顯,呈直視狀,造像配有環狀圓形覆蓮座、仰蓮座或束腰蓮座等不同造型樣式的蓮座。
桑耶寺石刻造像殘件鼻梁、鼻頭、冠頂和下頜受損,但不影響我們對人物神態的感知。造像表面平滑細膩,雙唇厚實,寬額窄頜,眼瞼下垂,呈冥想狀,膝下沒有配備蓮座,配有厚重的方石作為佛像的坐墊,左右兩邊受損嚴重,以致雕刻在厚墊前面的藏文題刻遭到了損壞、兩邊文字不全。昌都芒康囊巴朗贊拉康內共有9尊石刻圓雕造像的遺存,除大日如來像為蓮花寶冠式外,其他八大菩薩像均為高桶式的頭巾(拉堆帽),周飾蓮花冠葉。雕像均著三角形大翻領的交領寬袖長袍,腰間束腰帶,八大菩薩之座均為高臺式的仰覆蓮座仰覆蓮間以柱狀蓮莖相接,[31]從突顯雕塑線感的手法和蓮座的樣式上體現了內地造像的影響,但是造像總體的風格樣式展現了較為典型的早期藏式佛像的風格特征,尤其頭戴的“拉堆帽”、三角翻領寬袖長袍、足蹬的卷頭長靴以及腰帶和腰間套著繩子對別著的雙匕首配飾均保留了吐蕃贊普的典型裝束原貌。[32]相比之下,桑耶寺的石刻造像與香堆鎮向康的石刻造像更接近一些,但是,向康造像的眼瞼較為平直,下眼瞼下弧較明顯,呈直視狀,與桑耶寺新發現的石刻造像下垂的冥想狀眼瞼形成鮮明對比,應屬于兩處造像神態追求上的差異所在,也是所謂造像風格神韻的最大差異所在。從較為重要的細節上比較,造像有無頸飾吊墜、有無蓮座和有無白毫也成了兩處造像的不同點。雕刻技法上,相比昌都邦達囊巴朗贊石刻造像和香堆鎮向康大殿石刻造像,桑耶寺的石刻造像顯示其雕刻技巧更加嫻熟,雕刻手法細膩而大氣,向康造像內容豐富,有菩薩、明王和力士,同時也有供養人等,[33]但是其雕刻技藝略顯遜色,尤其囊巴朗贊拉康的造像雖然完整,但表現手法略顯笨拙、平直,線感強烈、而體感相對弱一些,而桑耶寺的石刻造像體感突出,僅從頭部就能夠感受到藝人對石雕技藝的駕馭能力。因此桑耶寺桑丹林周邊發現的這尊石刻圓雕造像極為珍貴。
? ??
??
佛教文化傳入青藏高原之前,我們所能見到的石刻藝術遺存主要是造型質樸、圖形簡潔的古代鑿刻巖畫,除此之外,極少見到本土苯教或其他宗教相關聯的造像類石刻,更見不到鑿刻于室外的摩崖石刻和造像碑等類型遺存,因此,吐蕃時期佛教石刻造像與來自高原之外的佛教造像師的活動有直接的關系。隨著佛教傳入青藏高原,諸多藏文文獻記載中較頻繁地出現了開鑿石雕造像的活動記錄,出現了各類造像摩崖石刻、石胎泥像等佛像題材作品,但是石刻圓雕造像的記錄及歷史遺存廖若星辰。筆者認為,對于歷史遺留的視覺產物,即使我們撿到的僅僅是一小塊石雕殘片,對于視覺藝術產物相關的歷史文獻研究者來說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可以說近年桑耶寺發現的石刻圓雕佛像遺存,填補了衛藏地區未見前弘期較大尺寸純粹石刻圓雕佛像的空白記錄。這尊造像從工藝水平上來說足以稱得上精品力作,從造型藝術的角度來說這尊造像的神韻、配飾刻畫技巧以及體積塑造能力等方面均展現出了較高的水準。這尊石雕即便是尼泊爾工匠所為,也是吐蕃的先輩們借用了尼泊爾嫻熟的工藝技巧,塑造了他們所需要的形象,其歷史價值、歷史意義不言而喻;其所反映的古代高原地區文化發展,各地、各民族之間自古以來已有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實,對當今相關學術研究所具有的參考價值也不言而喻。
[8]霍巍:《試析西藏東部新發現的兩處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9-15頁;霍巍:《吐蕃時代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第130頁。
[9]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西藏昌都察雅縣向康吐蕃造像考古調查簡報》,《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2輯),第27-42頁;張建林、席琳:《芒康、察雅吐蕃佛教石刻造像》,《敦煌吐蕃統治時期石窟與藏傳佛教藝術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42-355頁。
[10]韋色朗:《韋協》(藏文),第2003頁(相關桑丹林的內容與《??????????????????》內的記錄一字不差,完全一致,故不再重復記錄)“???????????????????????????????????????????????????????????????????? ????????????????????????????????????? ?????????????????????????????????????????? ???????????????????????????????????????”
[11]巴色朗:《巴協》(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48頁:“????????????????????????????????????????????????????????????????????????????????????????????????????????????? ??????????????????????????????????????????????????????????? ????????????????????????????????????????????????”
[12]娘·尼瑪韋色:《娘氏宗教源流》,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75頁。“二十六尊”之說似是筆誤。
[13]司徒·確吉加措:《司徒古跡志》,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44頁。本書成書于20世紀初,因此,這批造像很有可能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遭受破壞的。
[14]何周德、索朗旺堆:《桑耶寺簡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頁。從此處的記錄來看,貌似有兩尊石雕像,需要等待今后進一步發現。
[15]列謝托美等:《桑耶寺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頁。
[16]司徒·確吉加措:《司徒古跡志》,第182頁。
[17]“??????”指石頭。
[18]由于殘損較重,無法推測最初的本意,只能嘗試復原-但是沒有找到其他殘片或可信材料之前,所有的推測均不能作為信史資料使用:“父王赤松德贊在位時期開創了石頭上雕刻大日如來造像的習俗,天子赤德松贊仙逝后,為超度夫君亡靈,妃子赤莫列托人雕刻了這尊大日如來佛像。”
[19]韋色朗:《韋協》,第153頁。
[20]端智嘉、陳慶英:《贊普赤德松贊小傳》,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3頁。
[21]同上,第3頁。史書中對赤松德贊和赤德松贊的父子關系以及赤德松贊的稱呼別號有多種,但是依據當時期所立石碑上的信息,赤松德贊和赤德松贊是父子關系無疑,而且穆迪贊普(??????????????)、賽娜列景云(???????????????????)、赤德贊(????????????)、德松贊(??????????????),以及頂赤(?????????)等都為赤德松贊的別名。
[22]韋色朗:《韋協》,第153頁;巴沃·祖拉成瓦:《賢者喜宴》(上冊),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7頁。
[23]沈衛榮與侯浩然根據現存藏文文獻的梳理,對吐蕃贊普推崇大日如來信仰有以下闡釋:“赤德松贊與他的繼任者們試圖通過推行以大日如來崇拜為中心的儀軌與壇城,利用這種宗教崇拜曼荼羅表達的宇宙觀和意識形態來建立以贊普為中心的‘國家崇拜’,并通過民眾的宗教崇拜與觀想修行,使其內化成為集體潛意識的一部分,其根本目的在于構建以贊普為中心的一元政體來替代在神山的名義下不同宗族領袖以盟誓形成的多元政體。”沈衛榮、侯浩然:《文本與歷史-藏傳佛教歷史敘事的形成和漢藏佛學研究的構建》,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年,第108頁。
[24]端智嘉、陳慶英:《贊普赤德松贊小傳》,第13頁。
[25]司徒·確吉加措:《司徒古跡志》,第144頁。
[26]韋·囊賽著,巴擦·巴桑旺堆譯:《韋協》,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頁。
[27]這一時期的尼泊爾造像既仿效印度古典笈多風格,同時又吸收了帕拉王朝造像的表現手法,并融入了當地民族的特色,形成自己的風格模式。
[28]貢欽·晉美林巴:《晉美林巴文集》,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8-119頁。
[29]“斯烏蔡”黑石雕刻是一種小型石刻造像,大小尺寸在20cm左右,有高浮雕也有圓雕作品,主要流傳自尼泊爾和印度東北。
[30]巴色朗:《巴協》(藏文),第30頁記載:贊普赤松德贊修建烏孜大殿之初,首先修建了阿爾亞巴羅林殿,主體建筑完工后,贊普和堪布等人商量塑造什么風格的造像時,贊普說:“如果塑繪藏式佛像,定能使信奉黑教(在此指苯教)的吐蕃臣民皈依于佛教,請允許塑繪藏式佛像。”從《巴協》的這一記載中我們首次見到了“藏式佛像”這一說法(見38頁)。《韋協》中記載:贊普對甲蔡布堅(工匠)說道:“請塑造藏式佛像”,贊普認為“如果塑造與藏人裝束打扮一致的造像,定能使信奉黑教(指苯教)的吐蕃臣民皈依于佛教”,依遵旨意,舅臣(為了參考造像的裝束,聚集吐蕃臣民,塑造父性佛)中挑選帥氣的布達措、唐桑達略、瑪賽貢作為模特;為塑造佛母,挑選(身材優美的)覺如拉布曼做模特。通過《韋協》的這一記載,我們較為清晰地看到桑耶寺建造初期,為了解決復雜的社會矛盾,在吐蕃贊普的特別授意下,佛教造像師開創了本土民眾容易接受的佛像樣式,一種以借用本地區上流社會階層裝束為佛像裝束的嶄新佛像樣式,一方面借用了上流社會階層的“高貴”形象,另一方面解決佛教初傳藏地時民眾的生疏感,以最終獲得民眾的青睞而逐步達到傳播佛教思想的終極目的。
[31]霍巍:《試析西藏東部新發現的兩處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第9頁。
[32]這種裝束來自伊朗薩珊王朝,后期成為絲綢之路上的“特產”,隨著吐蕃政權統治區域的擴張,逐漸傳到了吐蕃社會,并似乎成為主流服飾。
[33]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西藏昌都察雅縣向康吐蕃造像考古調查簡報》,《西藏文物考古研究》(第2輯),第28頁。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者個人項目“西藏彩塑藝術遺存調研與保護對策研究”(項目編號:22VJXG011)階段性成果。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4年第3期

![]() 關注微信公眾號
關注微信公眾號
免費查看免費推送
- 西南林業大學
- 和靜縣第二小學
- 德州市醫療保障局
- 廣州市番禺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 河北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 福建招標
- 景縣騰維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 烏魯木齊市第九中學
- 徐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理委員會
- 準格爾旗薛家灣鎮人民政府
- 信陽醫院招標
- 合肥市蜀山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 海東市平安區農業農村和科技局
- 寧遠縣招投標中心
- 廣東省江門監獄
- 婁底|招標與采購招標網
- 丹鳳杰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 閩侯縣公開招標工程
- 婁底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
- 密山市招投標中心
- 沅陵縣招標
- 慶云縣政務服務中心
- 東鄉族自治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
- 深圳市福田區梅林街道辦事處
-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中鐵建工|集團第五建設有限公司招標信息
- 鄂爾多斯市東勝區市政事業服務中心
- 三明市招標與采購網
- 馬駒橋招標
- 浙江浙能科技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鎮江電力交易中心
- 廣東大舜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 合肥市安慶路第三小學
- 蕪湖市灣沚區陶辛鎮人民政府
- 遂平政府招標采購網
- 營口新世紀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
- 肥西縣上派鎮第五小學
- 合肥市重點工程建設管理局
- 昆山市鹿通交通安全設施有限公司
- 工信招標采購網
- 貴池區人民政府
- 運城市財政局
- 溫州市外國語學校
- 山東招標股份
- 臺州采購一體化泵站招標
- 松原供求信息
- 宜君縣招標中心
- 復興區人民政府
- 中國招投標項目網
- 煙臺采購招標網-煙臺招標網
- 中鐵七局第三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 易采網
- 大學科技園
- 開封市公共資源交易信息網
- 揚州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
- 嘉善公共資源
- 四川耗材招標
- 建材招標采購網
- 通化縣|教育局
- 漢中市招標中心
- 江干區招標
- 岳陽招投標監管網
- 北京市崇文小學
- 宣城公共資源交易服務網
- 廣西招標投標評標專家
- 合肥市琥珀山莊第一小學
- 國弘建設有限公司
- 清遠信息網
- 金融招標采購網
- 鄭州市鞏義市
- 夷陵區教育局
- 樅陽縣教育局
- 岳西縣財政局
- 陜西理工大學
- 哈爾濱林業大學
- 利辛縣政務服務中心
- 佛坪縣人民政府
- 咸寧招標網
- 沁陽市招投標中心
- 中煤|招標網招標公告